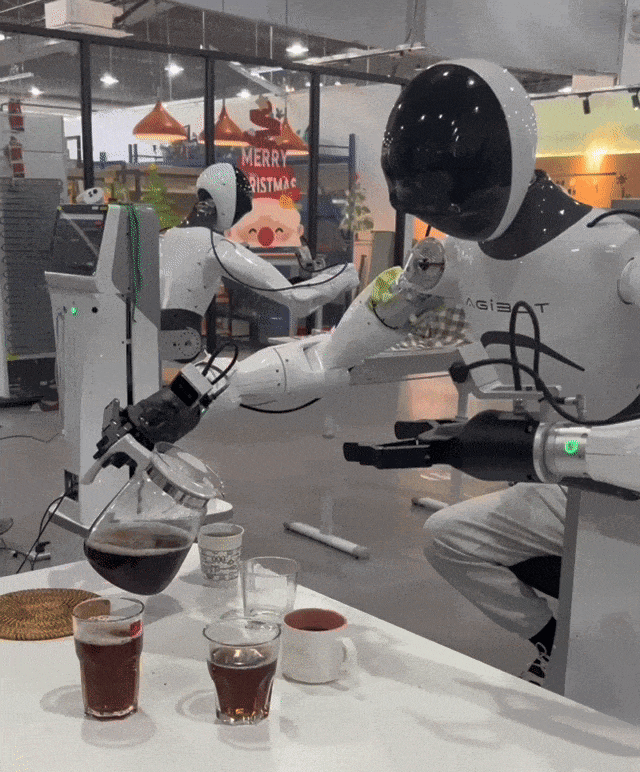
人形机器人作为“通用智能终端”的技术代表,被广泛寄予厚望。然而,在快速发展的产业实践中,人形机器人正面临多重挑战,包括当前关于其发展方向的核心争议——在技术百花齐放、应用需求多样化的当下,“人形”形态是否真的代表了机器人产业化的最优解?
通用性与场景扩展潜力巨大
与传统机器人不同,人形机器人的终极愿景是实现“通用性”。其设计理念源于“形态决定功能”的仿生学逻辑,旨在通过模仿人类身体结构,实现对人类环境的无缝适配与交互。支持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声音普遍认为,其最大优势在于“环境兼容性”与“技术复用性”,具有广泛的适应场景。
首先,从物理结构上看,人形机器人具备天然的空间适配优势。由于人类社会的物理空间和工具体系是为双足直立生物设计的,人形机器人可以“无缝”融入现有环境,实现上下楼梯、穿越狭窄通道、操作标准人类工具等功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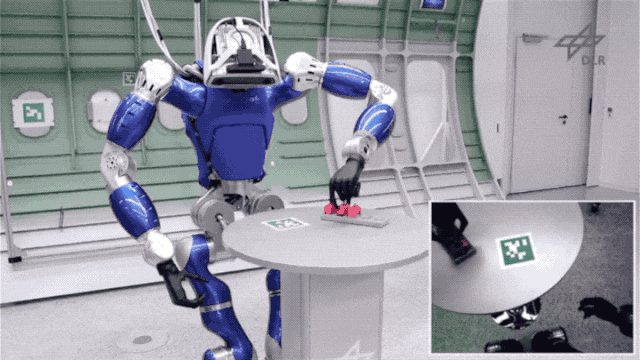
参与制造车间的搬运、检测,危险环境下的巡检与操作,如化工厂、矿井、核电站等。
其次,人形机器人还具备较强的技术复用潜力。以特斯拉为例,其将FSD(全自动驾驶)系统中的感知与决策算法迁移至Optimus平台,大幅降低了开发与训练成本。对于头部科技企业而言,人形机器人不仅是软硬件协同的技术集成体,更是其智能生态系统的重要延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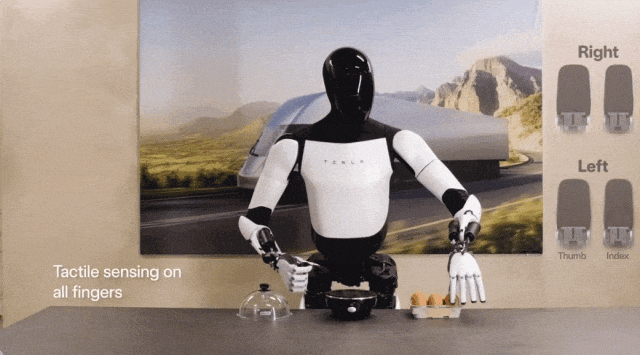
OPTIMUS 2.0的触觉系统借助汽车感应技术实现手拿鸡蛋。
此外,在家庭与医疗等高交互性场景中,人形机器人凭借拟人化设计和情感计算技术,展现出独特的“情感友好性”价值。相较非人形设备,这种融合物理护理与情感交互的能力,为人形机器人进入家庭场景提供了更自然的技术路径。

成为家庭看护、情感陪伴、智能家居控制、老年人辅助生活等的重要帮手。
成本、效率与可靠性三重困局
然而,技术发展的现实并不理想。批评者指出,人形机器人的通用性仍停留在愿景层面,其在成本控制、效率表现与系统稳定性方面均面临严峻挑战。
首先,硬件成本居高不下是人形机器人商业化的首要瓶颈。目前,国产人形机器人成本大约为70万元/台,远高于传统工业机器人。其核心部件如行星滚柱丝杠、空心杯电机等仍严重依赖进口,国产替代率不足,制约了规模化量产与供应链自主安全。
其次,人形机器人的续航与可靠性问题也广受诟病。从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事中可以看到,多数参赛机器人需中途更换电池,部分机型因关节过热甚至出现动作迟缓、失衡摔倒等状况,暴露了当前人形机器人在耐候性与平衡设计方面的短板,距离真正具备复杂环境下稳定运行的能力还有很长一段距离。

在北京亦庄半程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,网友戏称工作人员在为机器人喷“云南白药”的画面,实际是在为机器人降温。
再次,从功能适配角度看,人形结构在不少场景中反而显得“过度设计”。机器人形态的多样性由应用场景的差异化需求驱动,从工业制造到家庭服务,从极端环境到通用交互,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正推动技术革新与产业升级。

多轴机械臂机器人可用于汽车焊接、电子装配、金属冲压等重复性、高精度作业。
例如,在工业生产线上,AGV(自动导引运输车)与机械臂的组合不仅效率更高、成本更低,且故障率更低、维护更便捷。

移动运输机器人可用于仓储物流、工厂物料搬运、产线协同。
而在家庭中,扫地机器人、智能音箱等专用设备已能满足多数基础需求,远比人形机器人更具性价比与实用性。

扫地机器人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“标配”
此外,还有不少专注于极端环境与专业领域,技术门槛相对较高的特种机器人。
例如救援机器人可用于地震废墟搜救、核辐射区域探测、高层建筑消防。

医疗机器人可用于手术辅助、康复训练、静脉注射。

农业机器人可以参与农田自动化播种。

短期来看,结构简单、成本可控、应用场景明确的专用机器人仍将占据主导地位;而从长远看,人形机器人能否真正成为“通用智能终端”,关键在于多重因素的协同突破:一是硬件制造成本的有效控制,二是运动控制、能量密度、感知交互等核心技术的持续进步,三是大模型驱动的AI泛化能力,四是配套伦理和制度框架的及时构建。或许,真正的产业化成功,不在于“人形”与否,而在于能否以最低成本、最高可靠性解决人类社会的真实需求。
图源网络
·END·
作者:石淳瑜
编辑:赵佳文
编撰: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
监制: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、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
监审:同济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
